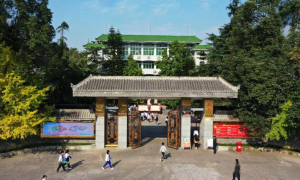7月17日,在阆中市妙高镇灵壁垭村,102岁的张先亨坐在藤椅上,目光落在央视13套新闻频道的画面上。当镜头扫过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,老人枯瘦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,喉咙里发出模糊的音节——那是他对峥嵘岁月最深情的回响。这位亲历了抗日战争、抗美援朝的老兵,用一生的故事,书写着他的忠诚与坚守。

战火青春:从农家少年到神炮手的蜕变
1941年夏天,阆中市妙高乡(现妙高镇)的玉米刚灌浆,18岁的张先亨被一纸壮丁通知改变了人生轨迹。经过3个月的军事训练,他成为了一名炮手。“军长总说‘炮是军之胆,你们要给步兵撑场子’。”张先亨的记忆碎片里,总穿插着这些细节。
张先亨所在部队最初驻扎在西安,任务是保卫这座古城的安全。“城墙根下扎帐篷,每天天不亮就练操炮。”张先亨的小儿子张仕保常听父亲讲,那时最难熬的是冬天,炮管冻得像冰坨,手碰上去能黏掉一层皮。
1943年深秋,部队接到命令开赴陕西三原县等地。张先亨记得,他们的阵地设在半山腰,透过望远镜能看到日军的炮群在河谷对岸闪光。“我们三炮一组,测距离、装炮弹、拉炮栓,动作不能慢。”张先亨回忆道。
最惨烈的一次战斗发生在河南。1944年春,他所在的炮兵排支援步兵进攻日军据点。“步兵往上冲的时候,日军的机枪像割麦子一样扫,上去一个连,下来只剩十几个。”张先亨的声音低沉下来,“我们的炮拼命打,想压住对方火力,可炮弹打完了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友倒下。”
1944年秋,张先亨随部队起义。“那一刻才明白,打仗不只是为了保家,更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安稳日子。”1945年,他在战火中入党。1950年,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,已是老兵的他主动请缨。在朝鲜战场上,他带着炮兵班在雪地里潜伏,炮管上结着冰凌,手指冻得发紫,却死死盯着美军阵地。“就像当年打日军一样,眼里只有胜利。”
1953年,一封家书让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红了眼——老母亲病重,盼他归家。“国已安,家有需。”他在退伍申请上写下这6个字,带着一身伤疤和一枚军功章,回到阔别12年的家乡。
老兵新传:把部队作风带到建设家乡中去
回乡后的张先亨成了村里最“懂章法”的人。乡里请他当干部,他二话不说答应了。“那时候村里穷,路是泥巴路,靠水靠天吃饭。”张仕保听村里老人讲,父亲当干部时,带头修水渠、整梯田,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出门,天黑才回家。
后来当了大队书记,张先亨更是把部队的作风带到了村里。开会从不迟到,说话直来直去,“谁要是偷懒耍滑,他眼睛一瞪,比炮口还吓人。”但他心肠热,哪家有困难,他第一个到场。
上世纪80年代,张先亨从岗位上退下来,重新拿起了锄头。“他闲不住,地里的玉米、水稻,长得比谁家都好。”张仕保笑着说,父亲总把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”挂在嘴边,这是他从战火里悟出来的道理。
如今的灵壁垭村,早已不是当年的贫困村。6年前新修的房子里,空调开着温度适宜,这是张仕保特意为父亲装的。他指着窗外说:“水泥路也通到了家门口。”
张先亨喜欢看电视。“国家大事他都关心,看到航母下水,他会拍着桌子说‘好’。”张仕保说,父亲下午要么眯会儿觉,要么看央视11套戏曲频道,《穆桂英挂帅》是他的最爱,“父亲说穆桂英能打仗,像他们部队里的女同志。”
“现在共产党领导,吃得好、穿得好、喝得好。”张先亨常拉着张仕保念叨。
老兵家训:“站有站相,坐有坐相”的军营式家教
张先亨的家教,严得像部队的纪律。五个子女从小就被要求“站有站相,坐有坐相”,吃饭不能吧唧嘴,见了长辈要问好。张仕保说,父亲常说“没规矩不成方圆”,这规矩里藏着的,是他对子女最深的期待。
这份严格,在对党的忠诚上尤为明显。“90多岁的时候,他好多事都忘了,却记着交党费。”张仕保说,“老爷子总跟我们几姊妹说,共产党让我们过上好日子,不能忘本。”
待人接物的礼数,更是刻在子女们的骨子里。7月17日,记者采访时,张先亨在采访间隙还问张仕保:“给客人倒水没?”张仕保说:“从小到大,父亲都教我们守规矩、懂礼数,‘客来敬茶,是本分’。”
2024年冬天,张先亨感冒了,躺在床上迷迷糊糊。子女们轮流守着,给他喂药、擦身。有一天他清醒些,拉着儿女们的手说:“你们要和睦,互相帮衬。”这话,和他年轻时教他们“兄弟姐妹要像战友一样”,如出一辙。
夕阳西下,张仕保推着父亲在院子里散步。远处的稻田绿浪翻滚,近处的水泥路干净整洁。“老汉,现在村子变化好大。”张先亨望着远方,嘴角露出笑意,喉咙里发出模糊的声音,像是在说“好,真好。”
这位百岁老兵的一生如同一本厚重的书,写满了烽火硝烟的勇毅,藏着归田守真的淡然,更透着家风传承的温暖。而那些刻在岁月里的坚守,恰是照亮后人前行的光。(南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易立权 文/图)